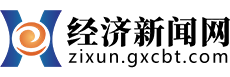姚斌/文
何谓“不确定性”?最早界定“不确定性”的定义来自弗兰克·奈特。1921年,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指出,可测量的不确定性与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截然不同。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根本不算是不确定性。对此,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他所谓的“不确定性”是指欧战爆发、20年后铜价与利率、新发明变得过时或1970年私人财富拥有者和社会地位的那种不确定。这些事情没有科学基础作为计算概率的依据,我们根本无从知晓。这就成为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才是所谓的风险,可测量的不确定性则不是。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奈特和凯恩斯区别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经济学家约翰·凯则在著作《极端不确定性》以“可解决”和“极端”不确定性来取代那种区别。“可解决”的不确定性是指可以藉由借阅来消除的不确定性,或是可用已知结果的概率分配来表示的不确定性。“极端”不确定性是指没有类似的方法可解决的不确定性,即我们根本不知道。
极端不确定性无法以概率来描述,不只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往往连可能发生的会是什么都不知道。极端不确定性不是指在统计学中的“长尾”,长尾是可以想象且定义明确的事件,发生的概率虽低,但至少估算得出来,例如轮盘赌连输好几次。极端不确定性也不限于纳西姆·塔勒布所说的“黑天鹅”,虽然黑天鹅是极端不确定性的例子。约翰·凯强调的是范围很大的可能性,介于两种世界之间:一种世界充满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但那些事件可以借助概率分配来描述;另一种世界充满意想不到的事件。极端不确定性的可能结果远远超出了金融市场,涵盖了个人与集体的决定,以及经济与政治的决定。
经济学家擅长解开复杂“经济模型”的难题。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就会颁给那些解开最难谜题的人。然而,商业、金融、政治、个人发展中的决策,以及决策所带来的结果大多过于复杂且定义不精准,不能以量化概率的方式来处理。它们受极端不确定性限制。
现实生活大多是落在随机性与黑天鹅这两种对立的极端之间。有时候,世界的真实状态是一个现在或过去的事实,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知道的。当问题是已知、但答案的范围无限时,套用概率的数学是可疑的,结果是模糊的。当问题已知、但问题的性质显示答案含糊不清时,我们无法合理地为状态估算概率。能够创造成长或波动的经济进程,不会长期稳定到让我们有效地估计经济变数的概率。多数有趣的总体经济问题,我们都无法轻易估算各种可能结果的概率,甚至连可能的结果都只能模糊地定义。因此,对于“未来10年有可能出现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吗?”这种问题的明智回答是“我不知道”。
贝叶斯定理的适用性
贝叶斯定理计算的是条件概率,即在B已经发生的情况下,A发生的概率是多少?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处理不确定的事件时,会赋予它一个先验概率。蒙提霍尔问题是贝叶斯定理的著名例证,依赖于所谓的“无差异原则”:如果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件事比另一件事更有可能发生,就要赋予每件事一样的概率。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谜题:有完全讲明的问题,也有已知的规则与明确的答案。然而,在一个极端不确定的世界里,问题很少是能够完全讲明的。蒙提霍尔问题一旦阐明了隐性与显性的游戏规则,就可以清楚解出确切的答案。很显然,贝叶斯定理能够处理有明确解的小世界问题。
先验概率是指根据以往经验和分析得到的概率,实际上就是主观概率。奈特与凯恩斯强调不确定性的重要。他们认为概率不能套用在已知或可知频率分配的领域(例如轮盘赌、死亡率观察、天气)之外。他们非常重视极端不确定性,但反对使用主观概率。主观概率的使用以及相关的数学,似乎把极端不确定性的疑团变成了可计算答案的谜题。而且,最热烈庆祝主观概率战胜极端不确定性的地方就是芝加哥大学,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人物莫过于米尔顿·弗里德曼。
巴菲特曾经以生动的方式表达他的投资策略:“我觉得股票投资是世上最棒的事业……因为你从来不需要被迫挥棒。你一整天只要等待你喜欢的球出现,然后趁着守备员打盹时,挥棒把球击出去。”如果概率构成经济决策的基础,那你确实“必须挥棒”,世人确实会愿意为每一种可能的赌注下注。但是,预期世人经常做这种交易显然是错的,谨慎的人从来不会想要那样做。像爱德华·索普那样少数专业的人之所以非常成功,是因为他们看出了异常现象或特别仔细地研究了明显的机会赛局的流程。
经济与社会系统就像天气系统一样,是非线性的。所以,经济的演变就像天气一样难以预测。而经济预测势必比天气预测更难,因为天气系统的根本物理性质有其平稳性的一面,而经济系统的基本结构却欠缺平稳性。经济的发展不受固定的物理运动规律所支配。虽然经济预测品质依然很差,但是为未来的经济进行规划还是有其必要性。因为企业必须做出投资决策,央行必须针对利率做出调整。
1944年,冯·诺依曼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中试图确立,概率推理可以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为理性决策提供一个连贯且严谨的构架。10年后,统计学家吉米·萨维奇在《统计学的基础》中为主观概率的存在寻找一个基础。萨维奇强调,这个基础只适用于“小世界”。大小世界的区别很重要,在“小世界”里,人们可以藉由追求期望效用的最大化来解决问题;而在“大世界”里,人们则是实际生活在其中。萨维奇小心翼翼地避免声称他的分析可以套用到他所谓的“小世界”的狭窄范围之外。类似蒙提霍尔问题都与“小世界”有关——都是可重复的机会赛局。然而,经济学家并未认同萨维奇针对其分析的应用范围所提出的警告。他们采用了萨维奇的假设,却宣称这样衍生的模型可以直接其使用在“大世界”的政策上。
于是,银行高管依赖风险专业人士的判断,而风险专业人士又依赖贝叶斯定理,结果令人失望。可以确定史蒂夫·乔布斯并没有使用贝叶斯定理,他知道他只能获得有限且不完全的资讯,他只是在等待“下一个大爆发点”。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这就是良好决策的方式,决策者努力思考的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此,约翰·凯质疑贝叶斯定理的适用性。
“小世界”模型的价值
1950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尔伯特·塔克编造了一个“囚徒困境”的故事。这个故事随后的理论化,使得囚徒困境成为最有洞见及成果的经济模型之一。建立模型的目的,是把一个疑团转变成一个谜题,也就是找到一个更简单的问题,而那个问题具有明确的解,且仍与实际问题有足够的相似性,所以能够让人产生洞见,启发最好的行动策略。这样的模型可以称为“小世界”模型,实用的经济理论通常都属于这种类型。亚当·斯密描述了以别针工厂的运作来阐述劳动分工的概念;大卫·李嘉图提出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模型。
塔克、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模型都建立在容易理解的描述上,其故事阐明了基本的经济概念。他们的模型可以用算式、数值范例或有趣的故事来呈现,而且应用在经济学上特别有成效。虽然这些模型无法为经济问题提供全面或计量的答案,但它们可以从“小世界”中举出类似的例子来说明,帮助我们建构论点,更了解疑团的本质。
有效市场假说是经济学中最有争议的模型之一。这个假说的基本见解是,可获得的公开资讯已经纳入证券价格中了。公开资讯或许大多已经融入证券价格,但公开资讯不见得总是或完全融入价格,所以投资者还是有可能设计出成功的投资策略。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与批评者似乎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都以为那个模型在描述“世界的真实样貌”。有效市场假说是一个模型的原型,它具有启发性,但它不是“真实”的。
“小世界”模型是一种虚构的叙事,它的真实在于微言大义,而不是具体细节。在经济模型中,“有代表性的行为者”“消费者”“公司”,但都不是真实的人或企业,而是一个人为的构想,每个细节都是作者的巧思,就像福尔摩斯的故事一样——是柯南·道尔发明的,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描述。经济学从简单的模型开始,这些模型以叙事的形式表达,有时包含一些假设的数字。经济史家约翰·克拉潘曾经这么批评《国富论》的作者:“很遗憾,亚当·斯密没有从柯科迪到几英里外的卡隆工厂去看他们制作大炮,而是去讲他那座无聊的别针工厂,那种别针工厂不过是座老旧意义的工厂罢了。”
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有效市场假说都是有用的模型,甚至不可或缺,但它们都无法描述“世界的真实样貌”。如果把这些金融模型当成现实来看待,以虚构的数字进行填充,并把它们当做重要决策的依据,那么使用这些模型就可能造成重大失误,就像它们在全球金融危机及许多其他场合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最终造成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覆灭。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极端现象大多源自模型外的事件。
我们很高兴自己了解这些“小世界”模型,我们也因为知道这些模型而变成更好的投资者,但我们不要把这些模型看得太认真,更不要相信它们是在描述“世界的真实样貌”。就连投资组合理论的创始者哈里·马科维茨也很清楚,他的理论只适用于小世界,但他的警告却大多被忽视了。
“小世界”模型的价值在于建构一个问题,以便为政策制定面临的“大世界”问题提供洞见,而不是假装能够提出精确的计量指引。我们无法从模型中得出概率、预测和政策建议。只有在模型的背景脉络中,概率才有意义,预测才准确,政策建议才有充分的证据。有意思的是,其他学科比较注意这样的问题。桥梁建造者和航空工程师处理的知识体系比较稳固,与先前经验不符的计量答案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这相当明智。然而,在经济学领域,每当有令人惊讶的结果出现,最常见的解释就是有人犯错了。在金融、经济、商业领域,模型从来就不是在描述“世界的真实样貌”,了解与诠释一个模型的输出,以及把模型应用到任何“大世界”的情况,永远需要有见识的判断。
沃伦·巴菲特、乔治·索罗斯和詹姆斯·西蒙斯代表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投资风格。他们都忽视甚至蔑视以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有效市场假设为基础的金融理论。事实上,那种理论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像现在那么成功。这些金融模型强调了所有投资者都应该知道的要点:多元化投资的好处,不同资产提供真正多元化机会的程度,以及资讯融入证券价格的程度。但经验告诉我们,在金融市场中获利不是只有一种办法,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只有一种方式,“金融界的真实样貌”不是只有一种叙事。有效的方法很多种,适合的工具取决于背景脉络以及投资者的技能与判断。我们确实可以从马科维茨的见解中受益,但我们从他的“小世界”模型中获得的见解有局限性。
面对不确定性的不同态度
演化论的发现是人类思想的开创性时刻。演化使人类学会应对在“大世界”中遇到的多种极端不确定性。面对不确定性的不同态度,影响了个人与群体的生存机会。在一些环境中,例如商业和体育界,行事谨慎、瞻前顾后就等于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而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甚至有可能是一种优势。在其他环境中,避免风险可能很合理。人类之所以存活下来,一个原因是我们祖先没有被掠食者吃掉。正如塔勒布所说的,演化偏爱那些存活下来的人。他们不见得是那些追求期望值最大的人。
如果我们生活在简单、静止的“小世界”里,最适化与解决“小世界”谜题的技巧就是演化成功的关键。但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生活在“小世界”里。在现实世界中,极端事件与生存息息相关。对个人来说,选择最有可能成功的策略可以尽量提高胜算,但这种追求最适化的个体所组成的团体,最终会被罕见的灾难所消灭。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曾经描述了这个道理的现实状况:种植最好的树会导致单一栽植,迟早会被前所未有的寄生虫所消灭。
人类之所以过得好,是因为我们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也因为理性没有唯一的方式。乐观对生存有利,要是加以控制引导,效果会更好。在赌桌上,过度自信往往是灾难,但对于激励队友、事业伙伴或军队的领袖来说却非常重要。
维珍集团的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是一位成功的冒险家。布兰森对现金流预算的具体细节不感兴趣,但他声称自己拥有一套看似毫无依据的成功系统。在“小世界”里,理性行为可以简化为数学运算,且那些运算是在问题界定清楚及充分了解环境的情景脉络中进行的。布兰森的成就让我们想起奈特在一个世纪前就提出但已被遗忘了太久的洞见:极端不确定性与冒险进取心精神的关系。诚如凯恩斯所言,当我们只依赖于数学期望值时,冒险进取的精神就会消失。冒险精神看似与公理型理性相悖,却是资本主义社会核心动力,是成功奥秘的关键部分。
极端不确定性与非平稳性密切相关。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稳定的世界架构让我们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并据此推断未来的行为。约翰·凯的批判并不局限在贝叶斯定理和经济模型,还延伸至行为经济学和参考叙事之中。无论批判的是什么,都并非意味着要放弃建模或放弃数学,而是必须明确它们的适用性。经济学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在于它是个实用的知识,而不是科学理论。因此,务实的经济学家的角色就会像消防员、医生和工程师一样,是解决问题的人。奈特知道极端不确定性会带来盈利机会,巴菲特、索罗斯和西蒙斯等人所累积的惊人财富证明了奈特的观点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