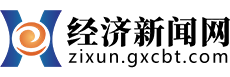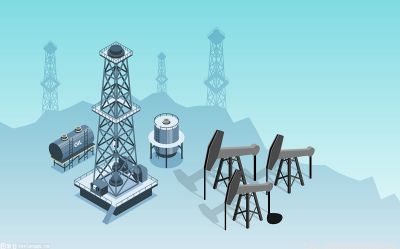(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1981年12月,冰心、夏衍、巴金(自右至左)摄于中央民族学院宿舍和平楼
记得那年,家乡来了亲人。有郭风,有何为,有舒婷和袁和平,还有谁,记不得了。他们应该是代表福建文学界来北京参加文代会吧,亲人们来自家乡,他们要拜访同是福建人的冰心先生。我和冰心是福州人,祖籍都是长乐,又同样都在高校,我在北大,她在中央民族学院。这样,我当然就充当了向导。记得是我委托韩晓征跟冰心先生联系的。我们到达的时候,先生已在书房等待我们。记得迎接我们的有吴青和她的先生,还有墙壁上梁启超先生书写的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题款是:冰心女士集定庵句索书,梁启超乙丑浴佛日。
落座之后是彼此问候。家人递上香茗,记得是来自家乡的茉莉花茶。来客们都说些什么记不清了。也许也是这一次,我和先生有过较多的交谈。先生知我祖籍是长乐谢家,她问我什么堂号?我记得少时家有灯笼上书“宝树堂谢”,便答:是宝树堂。先生听了,说:我家也是宝树堂。接着便脱口而出:“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临别的时候,先生持她与爱猫合影的照片赠我。照片不小,是当时流行的快印店家二寸彩照,猫咪偎依在她身边。
先生持照片停留片刻,翻转过来,她要为我留言。但见她举笔先写“谢冕”二字,接着写了“同”字。“同”字之后会是什么字?是当时流行的称呼“同志”?还是校园通用的“同学”、还是“同乡”?我有点紧张,我屏住气息。但见她轻轻一挥,竟是“同宗”二字!她记得“宝树堂”,记得我们同是祖居长乐人,她由此认定我们是一个祖先、同一个宗族,甚至是同一个家族!九十多岁的老人,她的思维如此敏捷、如此清晰,用字如此精到准确,不能不为之惊叹!这张照片,因为保留了先生的笔迹,甚至是保留了她活泼的思维,我十分珍惜。如同我所有的“珍藏”一样,如今“隐居”于何处,的的确确是找不到了!但我坚信它一定隐藏在某一个安全的角落,肯定会在某一天清晨或夜晚重现在我的身边。
在五四新文学作家中,我和冰心先生最亲近。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是同乡,又兼如今的“同祖同宗”,而是因为我最先接触的新文学作家是她,最先能够读懂并接受影响的也是她的作品。我觉得她的作品和我最亲近,甚至觉得她的《寄小读者》是为我们这些当年的小读者而写的。去国的情思,母爱、亲情、以及青岛海滨往事的追忆,还有她的优美、纯净的文笔,她无疑是我的第一个文学启蒙的老师。至于《春水》《繁星》,更是我早年学诗的范本。我曾说过,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冰心教我爱,巴金教我反抗”。她甚至是我人生和智慧的最早的开蒙人。我如今的抒情笔墨,是冰心给我的,我的文学情怀——爱心、亲情、人性和自由,也是受到冰心的启示的。
在北大,冰心曾是我的“邻居”。我留校任教后,最先的宿舍是十六斋,而冰心当年在燕京大学任教住的是燕南园。从十六斋到燕南园她和吴文藻先生的小楼,只有一墙之隔,步行用不了十几分钟。燕南园十几座小楼,是司徒雷登校长特为教授们建造的,一家一座楼,很是豪华。园中小径婉转,花木葱茏,静谧而优雅。在北大,燕南园是我最爱的地方,因为里边住着冰心先生和一些为我所敬重和景仰的前辈学者,这里也留下了我许多甜蜜的记忆。
冰心入住燕南园的时候还非常年轻,新婚,后来是推着婴儿车漫步湖滨。她的婚礼在临湖轩举行,司徒雷登校长是主婚人。司徒校长为人儒雅,充满爱心。据人们回忆,燕大的职工和教授家中有了喜事,婚礼,或是生日派对,他都会亲自出席致贺。司徒校长爱中国,他早年跟随父母来到中国,传教、办学,后来当驻华大使,他把全部的爱心和精力,甚至生命最重要的阶段、自己的青春都全部献给了中国。为办燕京大学,他赤手空拳,从选址、设计、四处募捐,到最后的施工,点点滴滴,都留着他的心血和爱心。离开中国之后,他晚景凄凉,身无长物。就连一个简单的遗愿,他只想把骨灰留在他所热爱的燕园,却不能如愿。
话题回到冰心。每次我回福建,下飞机的第一件事是拜望冰心文学馆。每次都是王炳根馆长亲自陪同。王炳根为我的这位宗亲做了许多工作。他甚至把我和韩晓征拜访过的先生的书房整座都搬到了长乐——连先生日常买菜的账单都不遗漏!我感谢王炳根,为他的敬业之心而感动。前些时我回到长乐,乡亲领我拜望了先生的长乐祖居,那里正在整理修缮。乡亲曾嘱我为旧居题字,我不敢。
2023年5月11日,于燕园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