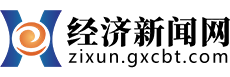文/陈根
不同于过去两年,由于奥密克戎传播极快,自3月疫情多点暴发以来,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广东、吉林、陕西,包括上海、深圳等重要经济中心都在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情况下,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封控措施,出于疫情防控需要,人们的社会生活也不同程度地转换至“暂停”模式。
不过,社会生活是暂停了,但生活还要继续,前所未有的封闭状态也让人们的互联网生活热闹得前所未有。不论是社区团购,还是平台抢菜,是接收信息,还是寻求帮助,互联网都成了人们与外界连接的重要窗口。
数字时代的数字生活与过去线下时代的物理生活有什么不同?当人们真正走向数字生活里时,成为数字时代的新移民时,人们的体验感又如何?
“附近”的消失和网络社会的崛起
“附近”的概念,源于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项飙认为,所谓“附近”,指的是以个人为圆心的周围实在的生活范围。就像过去的人们住在一个社区,会很自然地知道隔几个街道会有一个果蔬市场,转几个巷子会藏着哪个好吃的苍蝇馆子,大爷大妈们晚上会在哪儿跳广场舞。简单来说,“附近”是一种存在于你周围的、相对固定的、不能轻易改变的环境和一群人。
像以前的大院文化和胡同文化,就是典型的“附近”。每个人能够接触到的人都非常有限。除了上学时候的同学,上班时候的同事,还有家人朋友。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接触到的人和每个人的社会地位、阶级、爱好,都不会差得太多。在这种对“附近”的探索中,人与人的交往更为频繁、密切且深入。
然而,数字时代的降临,却改变了“附近”。随着现代社会“技术”和“资本”的不断驱动,导航、美团外卖、快递等现代便捷工具的出现,我们对于生活环境的认知完全可以依靠技术高度便捷的指引,“附近”正在逐渐消失。疫情带来的大面积的社会隔离就是一次例证,买菜靠盒马,学习靠网课、直播,获取资讯刷微博、微信,娱乐消遣点App,基本正常生活都能保证。
不仅如此,网络社会还在日渐崛起,不同于互联网之前的时代,互联网改变了过去既有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开放式的社交媒体,包括微博、推特以及Bilibili和Youtube这种以内容主导的“社区”,让人们轻易就能接触到和自己社会属性完全不一样的人。传统的距离概念被颠覆,屏幕以内的生活替代了过去人们能体验到的生活。
正如二十多年前,卡斯特尔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的第一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动态的全球经济已经在地球各处建立起来,将全世界有价格或价值的人及活动联结在一起,同时孤立与排除了节点外的社会大部分区段”“空间与时间,作为人类经验的物质基础,已经被转化了,流动空间支配了地方空间,无时间性的时间废除了工业年代的时钟时间。”
不论是“附近”的消失,还是网络社会的崛起,都向我们昭示了数字化生存时代的到来。按照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的解释,数字化生存即人类生存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生存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应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从事信息传播、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
尼戈洛庞蒂认为,数字化生存体现一种全新的社会生存状态。显然,当今正在形成的互联网文化,是一种渗透到全球平民生存领域方方面面的文化形态,它将给人们带来另类的生存体验。而疫情,则让人们真正感受到了数字化生存。
数字化生活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构建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数字世界,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从未有过的,但新鲜的体验却并非美好的生活。
项飙指出,“消失的附近”就是人们对周边世界是没有沉浸进去、形成一个叙述的愿望或能力。整个社会发展趋势也有一种“消灭附近”的趋势。而由于缺失了“附近”这个环境本身,一方面,人们的关注点自然而然地从以前的周围环境周围人周围事上更多地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更自我中心主义,关心自己的前途、发展,自己有哪些东西没有哪些东西。
究其原因,缺失了“附近”提供的支撑和保护,我们必须以个体的形式来面对庞大且复杂的世界,很多事情必须自己去解决。但面对今天世界的复杂性,以及现代社会生活压力的骤增,人们的幸福感并不必过去更高。
另一方面,在有“附近”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自发形成的,人们通过日常的生活都相互了解,不需要额外付出精力别人就会信任你,存在坚固的熟人关系网络。这是一个朴素的信任系统,这是一个原始但有效的担保机制,以中间担保人的信誉作为背书。个人一旦加入这个网,便会认识网中的其他靠谱的人,别人也会自然而然的对个人产生信任。
而“附近”的消失导致人和人之间这个关系网变得松散,人们逐渐丧失了一种自信,不再觉得能够构造出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因此,人们持续着日复一日的生活,成为数据的组成,以一种在一个社会的、世界的浪潮之下,无力地被后面的人推着往前走的生活状态生活着。
在单调且乏味的日常里,人们很容易认为,个人与本质脱离了关系,以至于再没有一种真实的、踏实的、充满意义的个体感受。这种“附近”的消失让我们生活的真实感锐减,不再有观望“附近风景”的耐心,它不再是一种整体地、深入地感知。这些“乏味”则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被不断加深、验证、加冕为一种“事实”。
与此同时,这也可能会让我们对“即可性满足”更为依赖,我们不再愿意花费时间去等待、去探索;还可能带来的是我们对“附近”容忍度的降低,更多的人选择了“背叛”与“逃离”,而这背后首先是意味着不了解,我们的感情自然无法真正地投入。
远离“附近”而走向“远方”的结果就是:人们逐渐发现,自己厌恶的东西越来越多,信任的人越来越少;需要的休闲与放松越来越多,专注却越来越少;快感越来越多,但充实感却不成比例地越来越少。
疫情也是一个重归“附近”的好机会
人类在历史上曾数次面临突发公共卫生危机,这些危机往往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一些城市或国家被摧毁,文明进程被改变,也加速了医疗卫生的发展,使人们有机会在危机中把握新机。疫情带来的封锁和隔离,虽然让人类社会朝数字化生存奔去,也让人们因为物理空间的限制有机会重新寻找和关心自己的“附近”。
近日,居住在上海的一位网友的分享引起网络热议:一位业主把可乐放在大厅分享给邻居,称“想喝的可以去拿”。随后,邻居们陆陆续续拿走可乐,也会留下辣酱、护肤品、方便面等物资。现在,“一箱可乐”变成了“一家小卖部”,摆放着宠物尿不湿、名贵护肤品、咖啡、啤酒等等。这一段邻里互助,被网友称为“疫情中的温暖与小确幸”。
“我尝有匮乏,邻里能相分。我尝有不安,邻里能相存。”一名业主在微信群里用一首元结的诗,记录下了这段特殊时期邻里间的暖心情谊。根据互联网,像这样的交换区,很多小区里都有。许多人在这里换到了急需的东西,暂时买不到也没那么急了。不可否认,疫情之下很多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但是挑战当前,团结就是力量,而每个小区里每个楼栋单元,就是抗击疫情最小的阵地。
上海疫情,也让很多年轻人第一次体会到邻里关系的重要性。疫情之前,人们穿梭于城市的混凝土里,邻里关系特别淡薄,都是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有的门对门的邻居,住了很多年,其实都没有说过两句话。现在,疫情让大家都困守在家里,很多人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远亲不如近邻”。
实际上,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技术化的到是城市化的过程里的某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新型的城市社区的出现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本消失的那些“附近”,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并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比如现在买菜的社区群参与网上团购,店铺辐射范围内都可以直接在家点外卖等等。
但事实证明,这种“附近”的连接不是必然消失的。卡斯特尔虽然从信息技术出发提出了“网络社会崛起”的必然,但同时也提出了远非技术决定论的论调。他认为,社会变革由技术本身引发,但是一旦成为系统,其内容就为发展的历史脉络所决定:“一个社会能否掌握技术、将技术内化,在充满冲突的过程中决定运用技术的方式,相当程度上塑造了这个社会的命运”。
在第三部《千年终结》的结语中卡斯特尔又总结道,“人性非本恶。万事其实俱可由提供信息、支持正当性、而为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所改变。”
“假如遍及全世界的人们信息灵通、主动、能沟通;假如企业能承担其社会责任;假如媒体变成使者而非信息;假如政治行动者对抗犬儒主义,以民主方式恢复新年;假如文化由经验来重建;假如人类遍及全球感受到物种的团结;加入我们由于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确立世代间的团结;假如在我们之间已取得了和平,并启程开拓我们的内在自我;假如所有这些都因我们的信息灵通、有意识、分享决策而变得可能,而时间之河仍在流淌,或许我们最终生活下去,爱同时被爱。”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数字化已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或许,也提供了一个让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刻都更有可能提醒自己去理解他人、去关心附近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