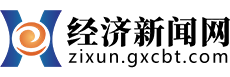作者 | 李北辰
来源 | 鲸落商业评论
从前有座山,山边有片海,海上有块大仙石。仙石自天地开始便吸收日月光华,一天山地迸裂,产一石卵,经风一吹,化作一石猴,石猴一蹦,目运金光,射冲斗府,惊动玉皇大帝。
齐天大圣孙悟空就此问世。
而如今的孙悟空,早已不再是这般往日模样。
孙悟空猴的外形,神的本领,人的秉性,给这个IP带来无限张力,为后人的改编,提供了广袤的创作空间。
因此在现实中,他也同样七十二变,从电影到电视剧,从动漫到游戏,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自《西游记》问世以来,孙悟空和师徒四人的形象就总在以各种形式出现。
西游,恰似一个老朋友,时不时就和我们叙叙旧。
说起悟空和西游,是前几天我看到一档名为《新游记》的综艺发布了以西游为主题的符号海报,并登上微博热搜。
嗯,距离吴承恩写出《西游记》已经接近500年,西游,仍是中国文化取之不尽的宝藏。
而这块宝藏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外创作者对这块宝藏的挖掘,都远比你想象中更为意义悠远。
时代变了,《西游记》就会跟着变
谈及对《西游记》的改编,永远绕不开86版电视剧《西游记》。收视率高达90%,重播超过3000次,统治了几代人的童年。同样是四大名著改编,其影响力远超同期的电视剧《红楼梦》和后来《水浒》《三国演义》。
为什么这样?
答案不一而足,我这里只挑一个易被大众忽视,却是近年来逐渐被学术界认可的原因,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86版《西游记》重建了当时人们对本土的认同。
这是个宏大的学术命题,我只能蜻蜓点水,举一个小例子。
众所周知,在导演杨洁的要求下,86版《西游记》都是实景拍摄——它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公路片”,剧组走遍了中国所有主要的景区,后人戏谑,所谓九九八十一难,全部发生在5A和4A景区里(五行山是云南的石林,盘丝洞是四川的九寨沟和都江堰,等等)。
这是导演组的有意为之,杨洁曾坦言:“我要通过‘游’字,把我国绚丽多彩的名山大川,名扬四海的古典园林,历史悠久的佛刹道观摄入剧中,增强它的真实感和神奇性,并达到情景交融,以景托情的效果。”
也因如此,86版《西游记》突出了《西游记》中的“游”,弱化了降妖除魔的“斗”。它有意契合了当时人们普遍的内在情绪,跟时代精神发生了某种共振。
事实上,这种契合和共振,无论在1986年以前,还是在1986年以后,都在反复上演。
青年学者白惠元在《英雄变格》一书中,通过分析从晚清至今无数版本的《西游记》改编,提出了一个非常敏锐的洞见:在现代中国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都有一个独特的孙悟空形象出现——也就是说,时代变了,孙悟空就跟着变。
没错,当时的人民需要什么,孙悟空就变幻成什么样的英雄:在晚清民国,孙悟空代表了中国进入全球化浪潮中的焦虑(当时有很多以《西游记》为主题的滑稽戏);在建国之初,他是反抗旧秩序的民族英雄;在冷战时期,他有能识别出关键矛盾的火眼金睛;而到了九零年代,他又成为独生子女一代的写照。
(图片来自:《大话西游》)
仅以大多数读者熟知的九零年代为例,九零年代后,《西游记》的改编风起云涌——然而,不同于86版孙悟空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到了90年代,孙悟空乃至整个《西游记》的改编色调,都因荒诞而显得更具灰度:在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里,他成了山贼;在何勇的歌词里,他扔掉了金箍棒,远渡重洋;在今何在的小说《悟空传》里,他成了“精神病”。
再一次,时代变了,孙悟空的形象就会跟着变。消费主义崛起,互联网时代来临,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代,信仰与幻灭,恐惧与慈悲,在那个时代纷至沓来,倏然之间,人们越来越能嬉笑着看待悲伤,亦越来越能庄重地对待笑话。
倘若一切意义都在消解,一切意义都可以被消解,那就干脆让孙悟空坠入凡尘吧。
你看,西游记的文化符号,在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一次次被翻译。
相似的精神内核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小说,电影,电视剧,到动画,游戏,综艺,不同时代创作者对《西游记》的翻译,总在不停变化载体。
比如,在综艺成为年轻人的文娱消费主要产品时,严敏导演的《新游记》就成了创作者的又一次致敬。
我一直觉得,一档好的综艺,宛若一盏明灯,能够将一个时期内的大众情绪全都显现出来。
从1990年的《正大综艺》,到全民投票的“超女”,再到全球化语境下的《天天向上》,直至“101”选秀体系,恰如学者周逵所言,综艺史就是一部社会观念史,好的综艺节目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思潮,并促发着我们观念和表达形态的变化。
而当综艺这种最活跃,最具弹性,最当下的社会文本,与《西游记》这个最经典的IP产生关联,或许会发生某种特殊的化学反应。
从目前已知的消息看,《新游记》类似一场借古言今的社会实验真人秀,按照官方介绍:“师徒六人(王彦霖、黄子韬、林更新、岳云鹏、张若昀、陈飞宇)沿着国道,经过小城,小镇,小村,用西游记的方式去旅行,看见最真实最平凡的中国。一次真正字面意义上的公路真人秀体验,一次用国道公路串起的大型田野调查,一次和自信前进中的中国普通人相互拥抱并相互激励的社会实践。”
嗯,如果说《西游记》的故事是求取世间真经,那么《新游记》的故事则是求“生活真经”——而所谓的生活真经,于我心里,或者说于这档节目的精神内核里,亦不过是“矿工诗人”陈年喜那本著名的书的名字:“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又或者亦不过是里尔克那句著名的诗句:“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在《西游记》里,师徒四人带着内心的愿望,踏上无尽的旅程,经历未知的磨难,体验人生的意义;在《新游记》中,六位平日被聚光笼罩的明星,同样需要“用二十一天完成一场人间历险”。
所谓“历险”,委实更像是“模拟人生”。
无论从官方预告透露的内容,还是从小红书上路透的内容,都不难窥见,《新游记》节目取景所去之处,皆为最具“生命气息”的平凡之地。例如,“师徒六人”体验当保安,当搬运工,当流水线工人,当房屋中介……说这些经历是“现代人的九九八十一难”不免有些虚夸——毕竟他们不是在“降妖除魔”,他们只是在平凡生活——但可以预见,这档节目的重点,是试图通过模拟人生式的异地体验,让主人公完成某种不一样的蜕变,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档节目和《西游记》有着相似的精神内核,那就是:人生如逆旅,这一路不存在什么简单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该节目出自被称为“内地综艺天花板”的严敏导演之手,综艺爱好者不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GQ曾在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在综艺导演中,严敏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高度娱乐化的节目里,严敏以一个‘作者’身份进行强烈的价值观输出,并借由亦真亦幻的理想世界,一次次呼应现实,让表达抵达最广泛的大众。”
可以预见,为了“呼应现实”,为了“抵达最广泛的大众”,更为了“致敬西游”,这档节目会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对“西游记”这个故事模板的现代化演绎。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西游
其实对《西游记》的现代化演绎,不只发生在中国,在亚洲乃至全球,西游的故事已经被讲了无数次,并且还将被讲无数次。
早在明朝,《西游记》就通过贸易商船进入日本和高丽。鸦片战争后,《西游记》被外国汉学家译成多种文字,流传欧美。
譬如在日本,单从风靡全球的漫画《七龙珠》里的人物设定,就能窥见《西游记》在日本的普及程度。1972年,《西游记》首个日语全译本发布,在日本引发一场西游热。此后几十年,无论是手冢治虫的《我的孙悟空》,尾崎红叶的《鬼桃太郎》,还是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都能看到《西游记》的痕迹。
不只在日本,西游在全球文化产业里均有自己的本国演绎。
(改编自《西游记》的美剧《荒原》)
这首先是因为西游故事的丰富性。
西游是个筐,所有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对于创作者,《西游记》委实有太多素材可用。九九八十一难,遇到的那些神仙妖怪,排列组合一番,几乎能满足任何类型的创作需求:神秘玄幻,公路奇遇,不羁爱情,异域文化等等。而且相比其他文学经典,《西游记》是少有的给出大团圆结局的作品。这种带着内心的愿望,踏上无尽的旅程,经历未知的磨难,体验人生的意义,最后皆大欢喜的故事模板,所有人都喜欢。所以它既可以是《西游记》,也可以是《新游记》。
其次,《西游记》对异域文化的包容性很强。
恰如一千个读者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虽然《西游记》中也有不少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但故事的内核是最简单的“正邪较量”,这让它的兼容性很强。譬如在澳大利亚翻拍的《西游记》中,孙悟空被塑造成一个中世纪骑士的形象,骄傲而奔放,这也非常符合中世纪西方骑士形象。
最后,《西游记》里的人物有着太强的可塑性。
在这个奇幻瑰丽的世界,师徒四人性格迥异,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贪嗔痴恨爱恶欲”,他们分别隐喻了人性的不同侧面,因此,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带入到西游的故事里,用他们的故事来讲自己的故事。
以孙悟空为例,戴荃创作的《悟空》,用如下词语形容悟空:“爱恨两难,肝肠寸断,且怒且悲,回头是岸,生死无关……”。你看,痛苦,愤怒,悲伤,后悔,看破,人生一切处境,在孙悟空那里都能找到替代。
这也是为什么,冥冥之中,我总觉得,中国最有名的IP ,从今往后一万年都叫孙悟空,都叫西游记。